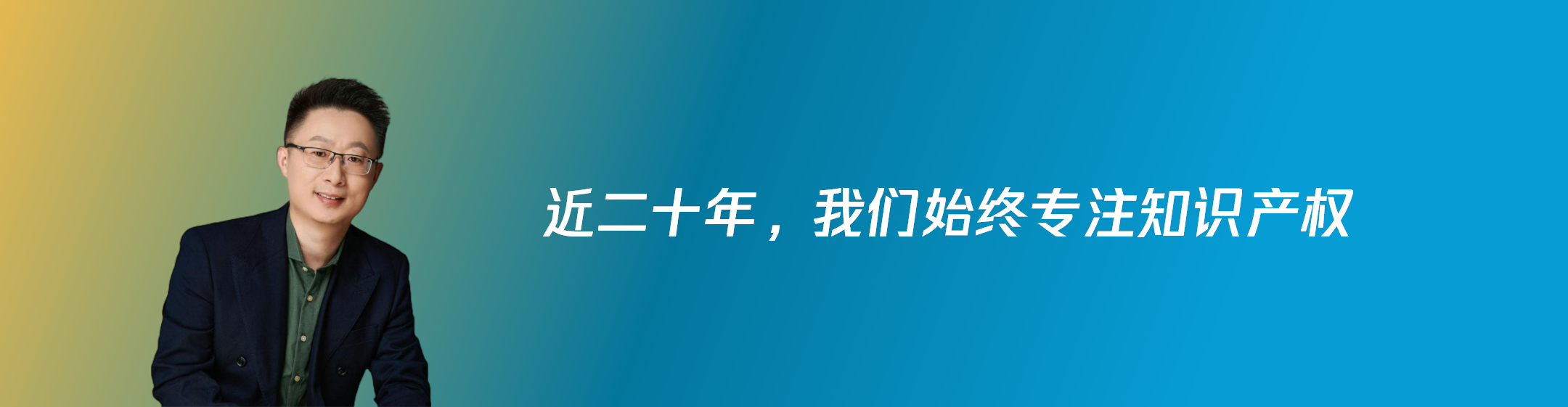作者|恒都知识产权事业部 软件著作权专业组 王清亮
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涌现了大量创新型企业,出现了很多因人员流动导致的纠纷,与之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诉讼率在近年不断地升高,很多企业管理人员在面对类似纠纷时往往无所适从。本文将结合几个案例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面临相关问题的企业有所启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任何未经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许可的软件使用行为,且该使用行为不在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之内,都应视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根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到法院起诉他人侵犯其软件著作权时,一般应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侵权的源程序、文档以及与之对比的原告的源程序、文档;
2、被告实施软件侵权行为的其他证据;
3、原告软件与被告软件的对比情况。
软件著作权与专利权不同,它仅保护软件代码的表现形式而不保护软件的编程思想。也就是说,软件著作权不具备像专利权那样的“排他性”,软件著作权人并不能排除他人就自己开发的相同软件再次享有权利的可能性。因此,法律规定对于软件侵权的认定原则为“实质性相似+接触”,即软件著作权人需要证明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认定被告侵权:
1、被告的软件与原告的软件相同或实质性相似;
2、被告接触过原告的软件。
“实质性相似+接触”原则,是外国法院普遍适用的软件侵权认定方法。实质性相似是指在先软件程序与在后软件程序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实质性的相似点,但因为两程序在实质上的相似并不能充分排除开发者各自独立开发出相似作品的巧合,所以在双方软件程序存在实质性相似的前提下,一般还需要同时满足在后程序开发者曾经接触过在先程序的源程序的事实,即在后程序开发者存在看到或者复制在先源程序的可能,法院才可推断在后创作的软件程序构成侵权。
“实质性相似+接触”原则在现有条件下作为判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存在与否的标准较为合理可行,因此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适用该判定原则,但法院在实际操作中,一般会在借鉴适用该原则的基础上,使用“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来源(或排除合理解释)”的评判原则,也就是说,即便两程序存在实质相似且在后程序开发人确实曾经接触过在先程序,但只要在后程序开发人能够对实质性相似部分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轻易认定为侵权。
运用“实质性相似+接触+排除合理来源”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案件审理中的直接证明,因为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案件中要证明是否存在复制行为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坚持对复制行为的直接证明,可能会导致原告因举证不能而败诉,使侵权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无法达到保护软件著作权的目的。
下面结合案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说明。
案例1、原告XXX信息技术公司诉被告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案:(2006)一中民终字第10460号
基本案情:XXX信息技术公司认为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的软件产品CyberVueAnesthesia与其享有著作权的ORIS软件相似,且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主要工作人员范XX、胡XX等人曾在XXX信息技术公司任职,具有接触到涉案软件的可能性,故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的该软件并非其独立开发,而是取自XXX信息技术公司。被告辩称双方软件仅在流程和功能上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证明被告侵权;原告称被告盗用其软件但无任何证据,原告以前的员工到被告公司工作是正常的人员流动,不是构成侵权的条件。双方都提交了软件程序进行技术鉴定,但由于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提交的源程序缺少工程文件而无法判定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源程序①与其提供的该软件的目标程序②是否一致。XXX信息技术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软件与被告软件具有一致性。
法院认定: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承认双方的软件在源程序和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并提交了自己的软件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但无法确定源程序与目标程序之间存在一致性。但鉴于范XX、胡XX等人曾在XXX信息技术公司任职,有接触涉案软件,故应视北京XX创新科技公司的软件并非其独立创作,认定为侵权。二审法院认为XXX信息技术公司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交反映被控侵权软件源程序或目标程序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的情况以及该软件是否销售或使用,进而也就无法判断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或目标程序或运行界面等与ORIS软件是否实质相同,因此, XXX信息技术公司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证明被控侵权软件与ORIS软件实质相同的初步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
因此,对于被侵权方来说,需要尽到初步举证义务,仅仅以被告接触过软件程序,而没有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一般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
案例2、原告XX在线北京公司诉被告XX天下北京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案:(2013)二中民初字第9903号
基本案情:原告XX在线北京公司是从事网络游戏及手机游戏研发与发行的互动娱乐企业,《XXX剑》是其开发和运营的一款手机游戏;被告公司的于XX曾在原告公司就职并参与了《XXX剑》的研发,之后到被告公司供职负责游戏开发。原告发现被告运营的手机游戏《XX传》复制、修改了原告《XXX剑》软件及源代码,并将修改后的源代码生成目标代码作为客户端程序进行公开的网络传播等。经初步比对二者绝大部分的变量名称、函数名称和类名称都相同,两款软件的相似度高达90%,《XX传》的执行程序中内含了多处属于《XXX剑》的隐藏文件、代码及拼写错误等。经法院主持委托鉴定结论也表明《XX传》是对《XXX剑》的抄袭。被告辩称: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于XX或被告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复制了《XXX剑》软件源代码,仅因于XX参与该软件开发就推定于XX复制其计算机软件源代码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游戏软件开发行业的实际情况;原告证明两款游戏软件相似度高达90%的鉴定报告存在根本性错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主张存在相似的文件夹名称、代码及拼写错误,不足以认定涉案两款软件实质性内容相似;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鉴定机构和人民法院提交的软件源代码的形成时间,不能证明其主张权利的软件形成时间早于被告公司的软件。
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委托原被告都认可的鉴定机构对二者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进行了鉴定,作为本案判断侵权事实是否存在的依据。根据对比鉴定结果,被告公司《XX传》游戏的客户端源代码的CS文件共有871个,原告公司《XXX剑》游戏的客户端源代码的CS文件共有834个,双方客户端源代码有463个文件具有对应关系,排除第三方客户端代码后,以原告为参考,客户端100%完全相同的文件共有66个,大等于90%小于100%的有46个,大等于80%小于90%的49个,大等于70%小于80%的25个,大等于50%小于70%的36个,小于50%的42个,来自第三方软件的199个。被告公司《XX传》游戏的服务器端源代码的.JAVA文件共有793个,原告公司《XXX剑》游戏的服务器端源代码的.JAVA文件共有951个,其中244个名称不同内容有相同或名称相同内容有修改。以原告为参考,源代码文件没有100%完全相同的,大等于90%小于100%的有33个,大等于80%小于90%的有38个,大等于70%小于80%的有53个,大等于50%小于70%的有58个,小于50%的有62个,没有来自第三方软件的文件。二者计算机软件部分源程序存在对应关系,被告公司未能就其源程序缘何与原告公司的源程序存在大量相同之处给出合理解释。结合于XX等软件技术人员接触过《XXX剑》软件代码,可以认定被告公司在编写《XX传》软件时将《XXX剑》软件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并以自己的名义予以发表,已构成对原告公司计算机软件的抄袭,构成对其著作权的侵犯。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软件比对是一个相对复杂、专业的工作,法院很难独立完成,一般需要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且对鉴定结果的依赖性较强。如果鉴定结果认定有部分内容相同或实质相同,而且被告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法院一般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3、上海XX电子公司诉沈阳XX电子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案:(2004)沈民四知初字第76号
基本案情:原告上海XX电子公司拥有xxxx门店系统的著作权,原告公司的职员张xx、叶X、冯XX和冯XX以个人股东名义成立了被告公司,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上述计算机软件私自使用,用于商业经营,并引用上述软件源程序创作某信息系统进行销售。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在计算机软件行业中,文档资料都存在相似的现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
法院认定:因操作手册是对软件如何操作、使用以及软件功能、特征的详细描述,被告未能提供某信息系统软件的运行环境,故可推定xxxx门店系统软件与某信息系统软件在功能上基本相同。又因被告公司股东曾在原告公司任职,有机会接触xxxx门店系统软件的源代码,因此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剽窃原告诉争软件的源代码等核心技术。被控侵权的某信息系统软件源代码,只有被告拥有,但被告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经法院释明,被告虽在鉴定过程中提供了某信息系统软件的源代码,但由于未提供验证服务器,目标程序无法运行,且被告承认其提供的源代码经编译后与法院保全的目标程序不一致,视为被告未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代码,致使法院无法对原告XXXX门店系统软件与被告公司的某信息系统软件源代码的相似程度进行判定,被告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即被告公司销售的某信息系统软件剽窃了原告XXXX门店系统软件源程序,被告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如果原告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在法院释明需要委托鉴定才能确认侵权是否成立时,被告没有充分的理由且拒不提供源程序进行司法鉴定,往往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当然,对于被诉侵权方来说,在对方仅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为据起诉侵权时,也不必被这张“纸老虎”吓住。《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上反映的有些内容是“华而不实”的,与客观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若能从软件名称、著作权人、开发完成日期、首次发表日期、权利取得方式、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方面提出质疑,辅以客观证据支持,也是有望扭转被动局面的;在有证据证明对方具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③时,还可以通过反诉要求对方赔偿因恶意诉讼导致的损失。
注释:
① 源程序,是指未经编译的,按照一定的程序设计语言规范书写的,人类可读的文本文件,通常采用高级语言编写。通过编译器可以将人类可读的程序代码文本翻译成计算机可以执行的二进制指令。
②目标程序,又称为“目的程序”,是一种计算机能够直接运行的程序,为源程序经编译后可直接被计算机运行的机器码集合。
③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一般至少包括:1.以提起诉讼的方式提出了某项请求,或者以提出某项请求相威胁;2.具有主观上的恶意,即明知其请求缺乏正当理由,以有悖于权利设置时的目的的方式,不正当地行使诉讼权利,意图使对方当事人受到财产或信誉上的损害;3.具有实际的损害后果;4.提起诉讼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