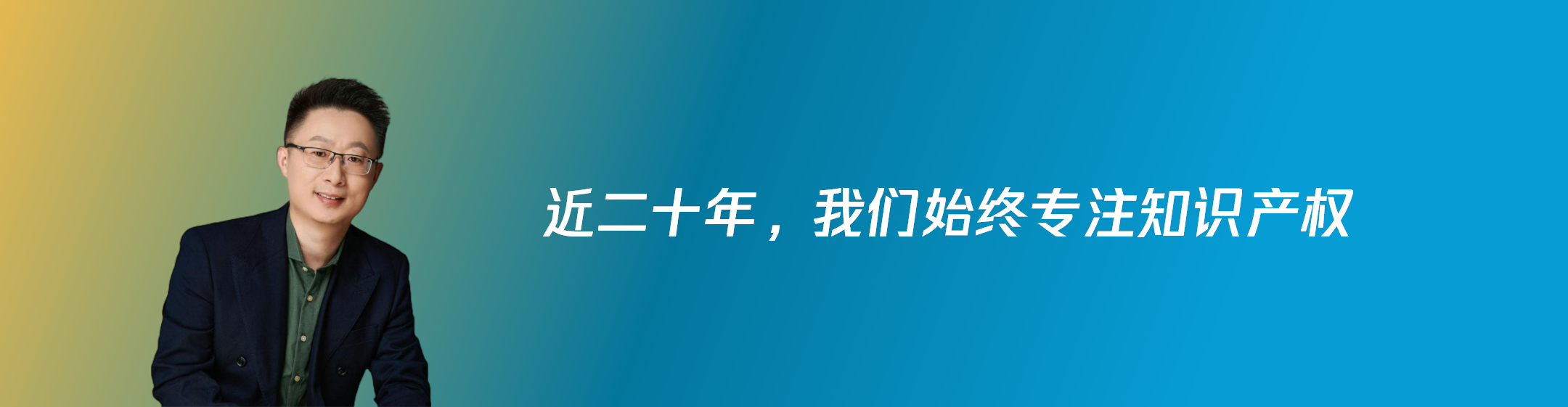作者:张洁琼 俞吟艳
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本次《解释二》的发布,距离最高院发布《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相隔近七年之久。其发布与近年来专利侵权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所涉法律问题触及专利基本制度和基本理念,专利及于市场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不无关系。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相继成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此次《解释二》的出台,契合了我国国家建设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主题。
《解释二》共31条。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权利要求解释、间接侵权、标准实施抗辩、合法来源抗辩、停止侵权行为、赔偿额计算、专利无效对侵权诉讼的影响等。在总体框架上,基本按照专利权保护范围、侵权行为样态、不侵权抗辩、侵权责任以及程序性事项进行排列。本文将针对其中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一、明确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认定,提高法院效率
《解释二》第14条至第17条用了四个条文的篇幅对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做了详细的解释,将我国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裁判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今后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便利。
1. 明确“设计空间”概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判定外观设计专利侵权主要依据的是《解释一》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明确了以“相同或相近类别产品”作为判断范围、以“一般消费者”作为判断主体、以“整体比较”作为判断方法。但在实践中,由于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有限,在面对较为成熟产品的外观设计时,以“一般消费者”作为判断主体经常会忽略“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议。
为了弥补这一判断标准的不足,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引入了“设计空间”的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发展较为成熟的产品设计空间较小,细微的变化就会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新面市的产品设计空间较大,形式和风格也较为多样,细小的差别就不会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解释二》第十四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肯定了“设计空间”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法院今后审理外观设计侵权纠纷案件中外观设计近似的判断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2. 明确成套产品、组件产品、变化状态产品外观设计的侵权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成套产品、组件产品以及变化状态产品的侵权认定一直是较大的难题。我国各地的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裁判规则,最高法院《解释二》将这些规则进行总结归纳,为法院对相关案件的裁判提供了便利。
对于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只要与其中一项相同或类似即构成侵权。
组件产品存在着组装关系唯一和不唯一的两种情况。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熨斗和底座组成的电熨斗,其使用价值往往在于组装之后的形态,因此应当保护其组合状态之下的外观设计。而对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例如积木、七巧板等,其使用价值则在于单个构件。由于其组合状态具有不确定性,对其外观设计的保护也应当立足于单个构件。《解释二》明确,只有在被诉侵权设计的单个构件与专利设计的全部单个构件一一构成相同或近似时,才构成侵权,缺一不可。
对于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认定侵权的方式类似于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也要求一一构成相同或近似才能认定侵权。
二、强调专利文书撰写的公示性,提升专利侵权的可预见性
1. 强调权利要求对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
《解释二》中的第五条、第十条分别规定了权利要求中的前序部分和技术特征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也即明确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应当属于专利授权确权阶段的问题而非属于法院司法裁判中所应解决的问题。此规定提高了专利文书撰写时撰写人的注意义务。另外,第十二条中规定,权利要求中采用的“至少”、“不超过”等用于对数值特征界定的用语规定若对技术特征起到了限定作用,法院对于权利保护范围的认定应当以该数值界定词语规定的范围为准。
2. 明确在侵权诉讼中法院解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相关文书
《解释二》第六条明确了法院可以运用于涉案专利存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及其专利审查档案、生效的专利授权确权裁判文书解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于09年最高院出台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增加了与涉案专利存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的相关文书可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的规定,并且在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上述相关文书的具体文件范围。由此,在扩大法院明确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所依据的文件范围扩大的同时,也使得依据的文件内容更为明晰。此外,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亦明确了禁止反悔原则的文件依据。
3. 当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存在明显歧义时对保护范围的界定
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当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存在歧义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得出唯一理解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唯一理解予以认定。此处强调了“唯一理解”。
和此条规定相关的典型案例之一即为“西安秦邦电信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诉无锡市隆盛电缆材料厂等侵犯专利权纠纷案”。该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如果权利要求的用语和说明书存在歧义,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根据说明书和附图的相应记载明确、直接、毫无疑义地修正权利要求的该特定用语的含义的,则可否根据修正后的含义进行解释?最高院再审审理认为: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存在明显歧义时,如果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权利要求相关表述的含义可以清楚确定,且说明书又未对权利要求的术语含义作特别界定时,应当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权利要求自身内容的理解为准,而不应当以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否定权利要求的记载,从而达到实质修改权利要求的结果,并使得专利侵权诉讼程序对权利要求的解释成为专利权人额外获得的修改权利要求的机会。
4. 对封闭式组合物专利侵权的认定
《解释二》第七条规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封闭式组合物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但该增加的技术特征属于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杂质的除外。”此条规定与历次版本的《专利审查指南》相一致。即他人的技术方案不得含有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所述特征之外的其他组分,除非是无法避免的常量杂质。根据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中药组合物专利被排除在上述规定之外。
和此条规定相关的典型案例之一即为“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特利尔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医药分公司与胡小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该案争议焦点在于被诉药品的说明书出现不同于专利产品的其他辅料,可否以此认定被诉药品不构成侵权?最高院再审判决认定:在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中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对于封闭式权利要求,一般应当解释为不含有该权利要求所述以外的结构组成部分或者方法步骤。上述解释与自1993年以来的《审查指南》的明确规定和长期的专利法实践保持了一致,也是对社会公众基于相关规定业已形成的稳定预期的尊重,有利于维护权利要求解释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对中医药做了例外规定。对该条的解读需要注意到药品专利的技术特点。一般而言,在机械领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中增加一个结构技术特征,并不会破坏原技术方案的发明目的,因此,机械领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的撰写较多采用开放式表达方式。相反,由于化学组分的相互影响,在化学领域发明技术方案中增加一个组分,往往会影响原技术方案的发明目的的实现。因此,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的撰写有采用封闭式表达方式的较大需求。因此第七条主要针对的是药品专利。而中药领域的组合物在作用方式、制作工艺、理化参数等方面皆与化学药物存在根本区别,将中医药作为例外规定不仅是从中医药本身的性质出发,也体现了本司法解释对中医药行业发展的促进与保护。
三、明确专利间接侵权,扫除灰色地带
根据《解释一》第七条规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认定专利侵权应采用全面覆盖原则。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这样一类专利纠纷:不法企业向消费者提供侵犯他人产品专利或者方法专利的产品部件,通过说明书等暗示消费者自己组装侵权产品。由于不法制造商回避了最后一个环节,根据全面覆盖原则就无法构成专利侵权。
为了规制上述行为,法院希望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对“共同侵权”的规定以及第九条对“教唆、帮助侵权”的规定,但也遇到了一定困难。一方面,“共同侵权”要求行为双方存在合意,而不法生产商在生产专利产品部件时与消费者之间并没有意思联络;另一方面,“教唆、帮助侵权”要求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而在上述情形下,消费者基于非生产经营的目的所实施行为很难被认定为专利直接侵权。
针对以上情况,《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上述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这一规定使得专利间接侵权突破了传统间接侵权的从属性,回避了消费者实施最后环节是否构成直接侵权的问题,也避免了间接侵权中所涉及的连带责任问题,对不法制造商进行了单独的评价。正如《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的说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外给予专利权人以额外的保护”,但确实能够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
四、提高标准专利许可效率,促进技术推广
标准必要专利是实施某项标准必不可少的专利。在某专利被纳入标准之前,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很难出现许可条件过高的情况。而在专利被纳入标准之后,由于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必须实施标准中所包含的专利技术,使得该标准技术的专利权人获得巨大的市场控制力,在许可条件方面就没有了市场的限制。在实践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许可过程中必须遵守国际通行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即FRAND原则。2014年1月1日,我国开始《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该规定首次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写入了FRAND原则。但该规定并未列明FRAND许可的内涵、费率和具体适用等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在现行法之下,一旦双方就标准专利的许可条件无法协商一致,专利使用人只能选择进行长时间的谈判或者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标准专利,并以FRAND原则进行抗辩。前者阻碍了专利使用人进入相关行业的进程,后者则有较大的法律风险。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当事人双方就标准专利的许可条件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交由人民法院确定实施许可条件。该规定将对FRAND原则在合同订立阶段的具体适用问题交由法院判断,提高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专利的应用与推广,有利于技术的进步。
五、缩短专利诉讼周期,确保专利权人利益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鉴于现行法规定的“民行二元分立”的诉讼框架,一旦被控侵权人就诉争专利向专利复审委员会另行提起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审理法院将因无权审查专利权效力而选择中止民事诉讼,等待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诉讼的结果。然而,由于专利授权确权的行政程序过于繁冗,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的情况更为突出,上述程序并不利于实质性解决纠纷。《解释二》第二条所规定的“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制度,使得法院可以在专利复审委作出无效决定后直接驳回起诉,而无需另行等待行政诉讼的最终结果。针对最终的行政诉讼结果,权利人可另行起诉。此种程序上的设计在缩短法院审理专利侵权诉讼周期的同时,也使得当事人在复审委无效决定被推翻之后可以另行起诉,亦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
此外,根据《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于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当事人可依据该决定申请再审撤销专利权无效宣告前人民法院作出但未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再审审查,并中止原判决、调解书的执行。此条规定旨在减少专利最终无效后因继续执行导致的执行回转,赋予该无效决定一定程度的对抗判决、调解书的效力。又因该专利无效决定尚未被司法审查,故为平衡专利权人与侵权人的执行利益,避免“中止原判决、调解书执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执行异议的规定,《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中止执行的情况下,专利权人可以在提供担保后请求继续执行。对此,侵权人则可通过反担保请求中止执行以制衡。当专利权被最终确定是否有效后,人民法院可执行担保或反担保财产,以避免执行利益落空。
文/张洁琼 俞吟艳
《统一细化专利侵权裁判标准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就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3/id/182673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3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3号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0号判决书。
同脚注[1]。
同脚注[1]。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