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知产力
作 者 | 钟 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申请或者注册的商标标志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案件,法院早就审理过。在1996年的“武松打虎”案中,被告山东景阳岗酒厂就是将已故画家刘继卣的一幅武松打虎图作为自己生产的白酒商品的商标予以注册,被刘继卣的继承人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①但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的并非这种典型的申请注册的商标标志使用他人作品,从而侵犯他人在先著作权的案件类型,而是在先商标注册人或者使用人依据其商标标志主张在先著作权保护,对他人通常是非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的与其商标标志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对应旧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前段的规定申请不予核准或者宣告无效的案件。后一种案件类型在最近几年也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1、这种主张在先商标标志的著作权以对抗在后商标申请或注册的案件,在商标授权确权诉讼之初并没有引起重视,尤其是对于其中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当时通常认为,在先商标权人主张对其商标标志享有著作权,提供了该商标的注册证,能够证明自己是商标注册人,就应当认定其同时是著作权人。比如在2005年的“上岛及图”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认为,因为原审第三人在先注册了“上岛及图”商标,因此其“对与本案争议商标标识相同的美术作品‘上岛及图’享有著作权,这是不争的事实。”②
2、但是,从2009年的“老人城LAORENCHENG及图”商标争议案等一系列案件开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变了做法,认为在先商标注册人的商标注册证不能证明其对该商标标志享有著作权,因为商标注册证上标明的商标注册人信息并非著作权法规定的署名行为,不能因此认定著作权的归属。③虽然“老人城LAORENCHENG及图”商标争议案的裁判理由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但是很快各级法院接受了该案的分析,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如何证明著作权归属的讨论了。
3、证明著作权的归属,自然应当根据著作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该解释中所列举的能够作为证据的文件,只有“著作权登记证书”④是比较容易、快速的取得,因此主张著作权保护的在先商标注册人就会在诉讼中将其商标标志登记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然后向法院申请著作权保护。比如在“百保力BABOLAT及图”商标异议复审案中,在先商标注册人就向法院提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及经过公证、认证的委托设计公司设计“BABOLAT及图”商标的声明及翻译件,法院采信后认定其商标标志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对诉争商标不予核准。⑤

4、著作权登记是自愿登记,对该登记的审查也是形式审查,因此上述案例中,当事人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外,还提交了设计公司的声明,虽然设计公司的声明单独作为著作权归属的证据证明力也不充分,但与著作权登记证书结合,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构成作品并确定著作权归属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有的案件中,主张著作权保护的当事人在诉讼中仅提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法院最终也予以认可。由此引发了更深一步的讨论。在“és”商标异议复审案中,在先商标注册人提交了对其商标标志进行著作权登记的证书,诉争商标申请人同样提交了对同一标志在同一家登记机构时隔仅一个月后进行著作权登记的证书,两份证书登记的标志虽然相同,但是著作权人不同,发表时间不同。⑥由此更加证明了,著作权登记并不进行实质审查,其证书并不当然具有证明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的效力。
5、随后,法院的判决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有的案件中仅有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法院认为不能证明著作权归属,因此不予保护;但是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又对仅提供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当事人给予了著作权保护。前者典型的比如“艾杜纱”商标异议复审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在“著作权登记仅进行形式审查的情况下,如仅因当事人在纠纷产生后进行了著作权登记而当然地认定其为著作权人,则意味着客观上认可了商标注册证对著作权权属的证明效力,这显然与法院对商标注册证这一证据效力的认定原则有悖。”⑦后者典型的比如“MECHAL NEGRIN及图”商标争议案,该案当事人在诉讼中仅提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其享有在先著作权,并对争议商标予以撤销。⑧

6、另外一种证明著作权归属的方式是:在诉争商标申请或者注册日之后取得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在先商标注册证。这种做法同样遇到了法院不同的处理。有的案件认可了这种组合的证明方式,给予在先著作权保护,但有的案件仍然不予认可。比如在“KP KIDS’S STUFF及图”商标争议案中,在先商标权利人也是在诉讼中提交了晚于诉争商标申请日的作品登记证书,但是法院结合在先商标注册证早于诉争商标申请日且诉争商标注册人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从而认定在先商标权人对其商标标志享有著作权。⑨但是在“TRUEAIR”商标异议复审案中,当事人提交了在后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在先在美国的商标注册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则认为,著作权登记证书的登记时间晚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日;美国的商标注册证不能作为享有著作权的证据。⑩

7、随后,当事人改变了上述证据在使用时的论证策略:在诉争商标申请或者注册日之后取得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仅证明著作权归属,在先商标注册证或者其他宣传使用证据则用于证明公开发表的时间即在先性。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比如在“CKH”商标异议复审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在先商标注册人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在先公开使用的事实认定其商标标志构成作品并给予在先著作权保护。?但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情侣图形”商标无效宣告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先在媒体上刊载的广告仅仅是对“情侣图形”这一商标的使用,并非对作品的“发表”,因此与诉讼中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都不能证明该图形的著作权归属。?

8、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在著作权归属证明方面争论以外,同时出现的还有是否构成作品的争论。因为主张在先著作权保护的那些商标标志大多比较简单,有很多是由单词、字母或者汉字构成,对于这些标志是否构成作品又与当时热列讨论的单个汉字是否构成作品纠缠在一起,更加显示出其复杂性。除前文已经引用的“艾杜纱”、“és”以外,下列标志,法院也最终未认定构成作品:
除前述的“BABOLAT及图”和“MECHAL NEGRIN及图”外,以下标志最终认定构成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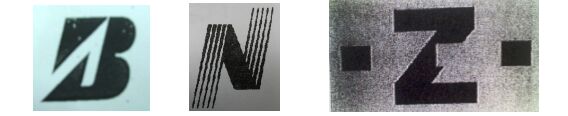
比较来看,未认定构成作品的标志和认定构成作品的标志实质上未必有不同,但最终处理结果不同,反应了裁判者对独创性标准的把握有区别。典型的是“艾杜纱”案一审判决、“CAMEL”二审判决和“超群”案再审裁定的意见。
9、在“艾杜纱”案判决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商标标志是否具有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其关键在于其“造型”是否具有独创性。一方面应考虑该造型是否给公众带来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亦应考虑这一造型所具有的智力创作程度不能具有过低的智力创作性高度。后者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如果对于智力创作高度过低的智力成果提供著作权法保护,将既达不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亦可能客观上不合理地占有公有资源并损害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各知识产权法律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商标标志构成作品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况下,因作品的保护通常不考虑载体也不考虑使用情况,意味着其可以不受商品或服务类别限制从而获得全类保护,即便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而被撤销的商标,亦可以基于著作权法禁止他人使用,对商标法相关基本制度构成了冲击。
10、在“CAMEL”案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所谓独创性的“高度”,实质上指独立创作但结果相同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较大,则独创性高度较小;如果可能性较小,则独创性高度较大,这只是为了方便司法实践中认定被告是否独立创作。在作品的表达非常简单,但被告确实能够证明其系独立创作的情况下,即使与公开传播的他人在先作品相同,也不能认为被告侵权,或者认为被告对其独立创作的作品没有著作权。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与商标权法对商标的保护各自独立,如果商标标志构成作品,著作权法依法予以保护,并不会对商标法的制度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商标标志具有独创性,表明各自独立创作但结果相同的可能性较小,作者以外的他人使用该标志申请注册商标,往往能够佐证其损害在先商标合法权益的恶意。著作权法的保护有时反而可以弥补因商品类似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而不能有效制止恶意注册的不足。一审判决认为,著作权法中对于作品的认定将会对商标法、专利法中的相关制度产生影响,著作权法对商标标志的保护可能对商标法相关基本制度构成冲击,但并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11、“超群”案再审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必须同时符合“独立创作”和“具有最低限度创造性”两个方面的条件,即不仅要求独立完成,还需达到一定水准的智力创造高度,智力创造性能够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判断与选择、展示作者的个性并达到一定创作高度要求,“独”与“创”缺一不可。?
12、最后,对商标标志的著作权保护,虽然除要求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外,还有接触等要件,但是调查所有通过在先商标标志著作权主张的或者支持其主张的案件就会发现,诉争商标几乎都是和在先商标标志完全相同的,近似的或者实质性相似的都非常少,因此在解决了作品和著作权归属之后,对于是否构成侵害著作权则是很容易解决的。
总结一下,目前关于商标标志在先著作权案件裁判标准极其混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标准可言,而且所有在著作权法可能使用的手段,比如要求著作权登记证书无意义、对发表的认定、对独创性标准严格要求、只有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标志才认定构成侵权或者避免著作权法与商标法在保护对象和目的方面的冲突等,法院都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尝试,引入了各种理论支持本判决的观点或者驳斥其他判决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尚不存在一个可以一揽子解决上述裁判标准冲突的方案。因此我们必须改换思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解决方案,这是本文下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注 释:
①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6)海知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一中知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高行终字第111号行政判决书。
③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行终字第1352号行政判决书。
④ 有的机构颁发的该种证书称为“作品登记证书”,以下按著作权司法解释的规定,统称为著作权登记证书。
⑤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终字第1270号行政判决书。
⑥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664号行政判决书。
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行初字第165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未上诉已生效。
⑧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483号行政判决书。
⑨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857号行政判决书。
⑩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576号行政判决书。
?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2357号行政判决书。
?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1408号行政判决书,该案尚在二审程序中。
?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1782号行政判决书。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周云川:《商标授权确权诉讼:规则与判例》,第355-373页,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第38号行政裁定书。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
